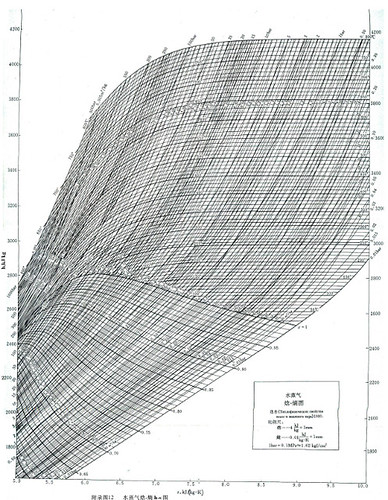昨天晚上义无返顾的从工行的提款机里取出了100块大洋,准备报国家计算机三级。取款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帐户里竟然有那么多钱,哎。说起报全国三级,也是一时冲动。既然咱江苏省二级都能考个优秀,说明咱还是有点计算机方面的天赋不是。不就是C语言吗,难是难了点,不过看一个暑假应该还能编个程序什么的吧。
今天上午赶鸭子竟然能得第五名,说是还能加综合测评,我想算了吧,都什么呀,什么都加,加了多没意思啊。其实走起路来脚脖子还是不灵活,都怪昨天体育课上测什么立定跳远。从小这东西就不是我强项。结果跳了2.45M,还被小朋友鄙视了一下。这家伙竟然能跳满分,晕啊,想她那身材,她那婴儿肥的脸,天啊。不过后来上肢力量考试还是不错的,双臂曲身做了19个,满分的。然后老师说下次课的技术考试考一分钟上篮。我再晕啊,这不是健康体育课的吗?不是考跳舞吗?哎,没想到又不是我强项,她咋就不考踢足球呢?哎,命途多舛啊。然后就是当天晚上十点多在新篮球场,我和肖文涛。结果又被这小子鄙视了一下。上篮,上篮,上篮……
前几天写什么关于党的什么材料,他们在我的群众材料上写我的缺点:话少,不关心别人……是啊,话很少,尤其在女生面前不知道说些什么;不关心别人,也是,从来都是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得很好,从来不会关心别人……看来还有的改啊。
手机不好用了,老出现白屏。